来源:保定晚报作者:时间:2020-12-18 09:43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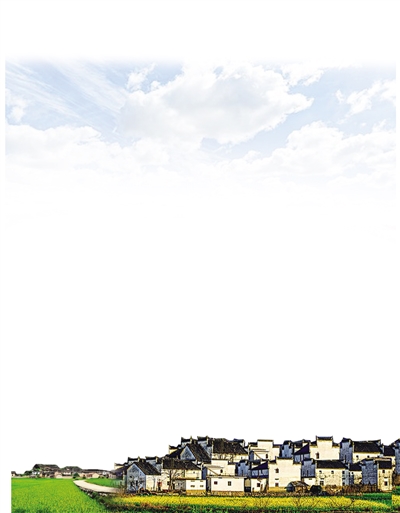
宋玉伯,43岁,家中有五口人。多年前,其父亲因脑血栓丧失劳动能力(2019年去世),母亲患病,不能干活。丈夫佟士义为“上门女婿”,平日在村里打工。家中两个孩子,一个读大学,一个读初中。因学、因病、缺劳力、无技术等多种原因致贫。2015年正式建档立卡,成为第一批享受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对象。2017年,实现脱贫。
脱贫户篇
□本报记者 杨宪敏 邸志永
12月15日,四面环山的易县骆驼峪村,冬日静好。
村南一处面积不大的院落,盖有四间平房,一只小花狗见陌生人进门,叫个不停。屋檐下堆着收获的玉米,阳光之下分外金黄。宋玉伯家,是小山村最普通的脱贫家庭之一。
院子西侧的两个窗纱围起来的简易鸡棚里,几十只公鸡正在进食。就在前年,她和丈夫还在山里养柴鸡,并将之当成了日后发家的路子。
“第一年还成,挣了点钱。第二年就碰到问题了,黄鼠狼太多,养了150只鸡,等到长大的时候,剩下不到60只。”提起养鸡,宋玉伯一脸无奈。
好在,性格直爽的她,又选择了新路。
“生活就是这样,政府帮咱们脱了贫,但将来致富,还得靠我们自个儿努力。”43岁的宋玉伯,不肯“等、靠、要”。
堂屋的茶几上,摆满了十来种小零件。“不去打工的时候,做点小手工。”宋玉伯拿起桌子上做好的成品,放到一旁的箱子里。
“这是帮人加工的密码锁。天一冷,空闲的时候多,闲着也是闲着。”她笑呵呵地说。
“三种弹簧、两种扣子、左右两个开关、两个贴片、前壳后盖……”宋玉伯一边介绍一边做,不一会儿工夫,一把锁便完成了,“做一个差不多40秒吧,一箱大概四五天能完成,赚50块钱。”
说话间,宋玉伯的丈夫佟士义推门进了屋。
“刚从山上回来,天儿是越来越冷了。”这个不善言辞的中年汉子,说起话来有些腼腆。今年,在帮扶干部支持下,他成为了村里的防火员,每年收入3600元。对于这个公益岗,他非常珍惜,没事儿的时候,就到山上转转。
脱贫之后政策不变,宋玉伯在扶贫干部协调下,还是村里的保洁员,每年收入3600元。
“前两天,去果园剪枝还剩一些活,一会儿我过去把它们剪了。”宋玉伯给佟士义交代了一声,拿起剪枝刀推起三轮车便往村东头走去。
出村不远便是果园,宋玉伯拿起剪枝刀熟练地修剪起来。
“这是苹果树,结出来的苹果又脆又甜。”宋玉伯说,村里的土地如今多变成了果园,他们不出村便能打工。
趁着休息的空档,宋玉伯聊起了前些年家里的苦日子。
“那时候孩子小,我们俩不能到离家远的地方去打工,一年到头也就挣1万多块钱。父亲生病花去近20万,家里的积蓄花没了,还拉了不少饥荒,日子苦得不行。”宋玉伯说,那时候孩子想买个小零食,她都舍不得。
2015年,宋玉伯一家迎来转机。
那一年,骆驼峪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,发展苹果产业。宋玉伯一家将1亩多地流转给了合作社。夫妻二人从繁杂还不赚钱的农活中解放出来,到果园打工。
宋玉伯称,两口子在果园干活儿,一天能收入150多元钱,一年打工160天,大概能挣2.4万元。加上其他地方打零工的收入,每年大概能挣3万元左右。
两口子打工收入加上公益岗等帮扶政策性收入,2020年家里人均年收入8870元。
脱贫摘帽不是终点,而是新生活、新奋斗的起点。
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,宋玉伯一家在2017年脱贫摘帽后,第二年专门养起了柴鸡。
“我丈夫在老家安格庄乡东古县村有块山坡,我俩2018年学习了养鸡技术,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下,在山坡上养起了柴鸡。”宋玉伯称,借助当地太行水镇等蓬勃发展的旅游业,柴鸡的销量很不错,第一年便实现了盈利。
没想到,鸡多了,也引来了黄鼠狼。
“为了斗黄鼠狼,我专门买了大鹅,结果还是挡不住。”眼看着鸡一只只减少,实在“斗不过”黄鼠狼的宋玉伯,不得不放弃了山坡养殖。
其实,养鸡收入还可以。想着明年继续养鸡的宋玉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:一只柴鸡卖到100元左右,成本价近70元,一只利润在30元左右,300只的利润差不多有1万元。
如果加上夫妻二人的公益岗每年7200元,在果园及工地打工的3万元收入,再加上光伏产业分红……一家人的富裕路近在眼前。
为此,记者专门咨询了专业人士,给宋玉伯山坡养鸡提供了一个小窍门:在鸡舍里装上强光线的LED大灯,专门在晚上开着,让夜间活动的黄鼠狼进鸡舍心有顾忌。同时,在鸡舍里养上狗和大鹅,多增加两道保险。
“我先少养些鸡试试,如果三道保险管用,再扩大规模。”宋玉伯说,养鸡要是能继续,欢迎记者明年再来,尝尝她的“致富鸡”。
这个朴实而乐观的妇女,已经开始憧憬明年继续养鸡的事儿了。